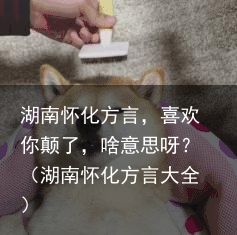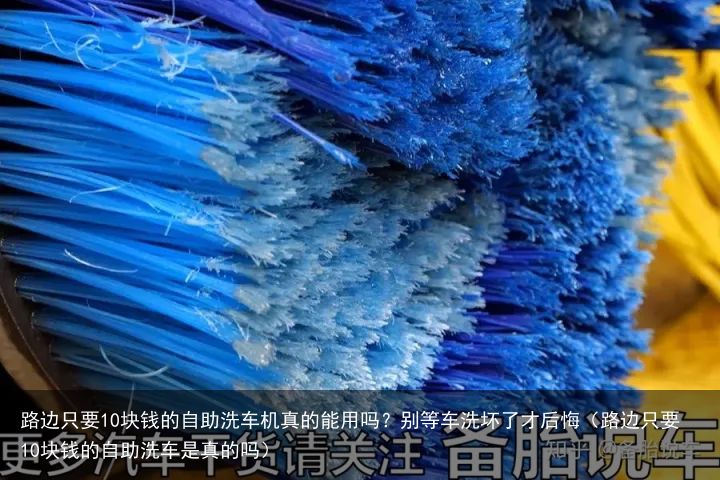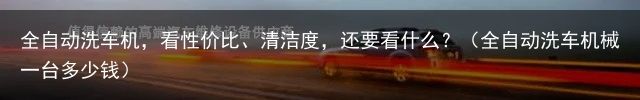摘要:湘语主要分布在长沙、湘潭、株洲等湖南中部区域,包括长沙市的城区、长沙县、望城县的全部以及宁乡县和浏…
湘语
主要分布在长沙、湘潭、株洲等湖南中部区域,包括长沙市的城区、长沙县、望城县的全部以及宁乡县和浏阳市的部分地区,株洲市的城区和株洲县,湘潭市的城区、湘潭县、韶山市和湘乡市,岳阳市的城区、岳阳县、汨罗市以及湘阴县和平江县的部分地区,常德市的安乡县的部分,益阳市的城区、南县、沅江市、桃江县和安化县,衡阳市的城区、衡阳县、衡山县、衡东县、衡南县和祁东县,娄底市的城区、涟源市、冷水江市、新化县和双峰县,邵阳市的城区、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武冈市、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及绥宁县、洞口县和隆回县的部分,怀化市的辰溪县、溆浦县和会同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永州市的城区、东安县、祁阳县、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新田县的部分地区。
西南官话
在湖南是第二大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区域,包括常德市的城区、汉寿县、桃源县、石门县、临澧县、澧县、津市市、华容县以及安乡县的部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市、古丈县、保靖县、花垣县、凤凰县和龙山县,张家界市的城区、桑植县和慈利县,怀化市的城区、中方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通道、新晃、芷江3个侗族自治县,永州市的城区、东安县、双牌县、道县、江永县、新田县、宁远县、蓝山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郴州市的城区、桂阳县、宜章县、临武市和嘉禾。
赣语
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包括岳阳市城区、临湘市和岳阳县、平江县、华容县的部分,长沙市的浏阳,长沙县北,株洲市的醴陵市、攸县、炎陵县和茶陵县,衡阳市的耒阳市和常宁市,郴州市的永兴县、安仁县和资兴市,邵阳市的洞口县以及绥宁和隆回的北部。
客家话
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和东南部,包括岳阳市的平江县,长沙市的浏阳市,株洲市的醴陵市、炎陵县、茶陵县和攸县,永州市的江永县、新田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郴州市的汝城县、桂东县、资兴市、安仁县、汝城县、桂东县、临武县和宜章县。
湘南土话
著名语言学者杨时逢认为,湖南南部的衡阳、郴州、永州三市(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分别称衡阳地区、郴州地区、零陵地区)通常被称为“湘南地区”。这一地区东与江西省、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与广东省交界。其中的永州市、郴州市境内的不少县市,包括永州市所辖的零陵、冷水滩、东安、双牌、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10县区,郴州市所辖的桂阳、嘉禾、宜章、临武、汝城、资兴6 县市,一共 16 县(市、区)存在一些与当地的“官话”截然不同的“土话”,我们统称之为“湘南土话”。
代表方言:一,以资兴说(Zixingsa)为代表的土话区(白说),包括永兴、桂东、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话与客赣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话为代表的湘南土话双语区,包括宜章、临武、嘉禾、桂阳、蓝山、宁远,是同时使用湘南土话与西南官话的双语区。三,以道州话为代表的保留了湘语特征较多的湘语土话,包括冷水滩、零陵、东安、双牌、道州、新田、江永、江华与桂北平话关系密切。
瓦乡话
瓦乡话主要分布在怀化市的沅陵县、溆浦县、辰溪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古丈县、泸溪县。
其他
以上分类是粗线条的分类。有的区域是双方言区域,例如永州和郴州通行官话,局部地区并行土话和其他方言。有的具有混合方言特点,例如:岳阳城区方言有赣语和湘语混合的特点。湖南中部的新化县等地方的方言也有这个特点,虽然一般把它们归属湘语。湖南东南部和西部的不少方言,例如永州城区的方言具有官话和湘语混合的特点。衡山县除了北部靠近双峰的“后山话”是典型的湘语,大部分地区说的“前山话”从语音等特点来看具有官话特点,是湘语和官话的混合。例如,古代全浊声母在现在前山话中清化以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长沙市区用“爹爹”称呼爷爷,然而浏阳、衡山用“爹爹”称呼爸爸。
少民语言
编辑 播报湖南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苗语、土家语、侗语、勉语以及壮语。
苗语
苗语湘西方言
湖南境内的苗语主要为苗语湘西方言(dut Xongb),属于苗瑶语系苗语支。苗语湘西方言又称作苗语东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苗族聚居区和贵州松桃县等地。说苗语湘西方言的人口约100万。苗语湘西方言分为两个次方言,以其西部次方言花垣县吉卫镇腊乙坪村的语音为标准音。于1950年代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湘西苗文。杨再彪(2004)把湘西方言分为东西两个次方言,西部次方言分布在凤凰县、花垣县、吉首市南部、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东部次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古丈县、龙山县南部和吉首市东部等。
土家语
土家语(pi˧˥ tsi˥ sa˨˩)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在土家语中,土家族人自称pi˧˥ tsi˥ kʰa˨˩ [毕兹卡]。 根据杨再彪博士2011年4月提供的数据,土家语目前在湖南省西部的34个乡镇中、200个行政村的500个自然村寨中依然被使用着。土家语分为南北两种方言。南北土家语音韵语法词汇差异过大,无法交流。
土家语北部方言又称毕基语,为以前绝大多数土家族人的母语。但现在,许多土家族人的母语已转为了湖南西北部当地流行的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只有少部分土家族人的母语仍为土家语北部方言。
龙山土话
龙山县:洗车河镇、苗儿滩镇、靛房镇、洛塔乡、干溪乡、猛西乡、凤溪镇、坡脚乡、他砂乡、内溪乡、贾市乡
永顺县:对山乡、和平乡、西歧乡、首车镇、勺哈乡
保靖县:普戎镇、仙仁乡、涂乍乡
古丈县:茄通乡、断龙乡
保靖土话
龙山县:隆头镇、岩冲乡、长潭乡、里耶镇
保靖县:隆头乡、比耳乡、马王乡、拔茅镇、昂洞乡、龙溪乡、簸箕乡
孟兹话
土家语南部方言又称孟兹话。孟兹话为土家语在大面积的苗瑶、汉语区内的方言岛,自古以来便只有很少的母语人口(现仅几百人使用),分布在泸溪县境内的潭溪镇且己村的九个村寨(别名九寨话),潭溪镇中也有少量迁移人口。具体村寨名为(括号中为该地孟兹语名):
下都(tsʰie˨˩ bu˨˩)
铺竹(pʰu˧ dzɯ˧)
波洛寨(bo˧ lo˧ tsai˩˧)
且己(tsʰa˧ dʑi˧˥)
下且己(tsʰa˧ dʑi˧˥ a˨˩ di˧˥)
大波流(tsʰie˨˩ dɯ˥ pʰo˨˩)
小零寨(tsʰie˥ ȵĩ˧˥ sa˧)
梨木寨(li˨˩ mu˨˩ tsai˩˧)
土麻寨(tʰɯ˩˧ ma˨˩ tsai˩˧)
潭溪镇(hu˧ dɯ˧)
侗语
侗语(sungp Gaeml)是侗台语系(或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的语言之一,现使用拉丁字母的侗文(leec Gaeml)。侗语南北两种方言皆在湖南有分布。在湖南省内,侗语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的通道陇城、新晃中寨和靖州滥泥冲等地。
勉语
勉语(Iu Mienh)是瑶族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也是苗瑶语系瑶语支唯一的语言。勉语内的勉方言(湘南分支)以及藻敏方言在湘南的瑶族聚居区使用。其中勉方言(湘南分支)分布在湖南南部山区的瑶族聚居村落,使用人口超过13万;而藻敏方言仅在湘南的宜章县内有分布。
历史形成
编辑 播报湘语
秦统一中国之后,实行郡治,分设长沙郡和黔中郡,而长沙郡的范围也深刻的影响了今天现代湘语的版图,对于湘语的传播,发展和维护其内部的一致性,无疑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古汉语与少数民族杂糅产生的南楚语则是古湘语最早的源头。 [2]
具体地说,秦汉时期的汉族主要分布在3个区域: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水和澧水中下游地区;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湖南和江西两省的交界线一直到广东省的狭长地带。唐朝后期刘禹锡贬谪到武陵以后有文章说:“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全唐文》第六〇三卷的《上杜司徒书》)说明当时湘江、沅江流域还有大量非汉族地区,汉语难得听到。湖南境内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汉族人从原来居住区域向周边地区迁徙相对便利,因此这种逐渐扩散方式的移民运动历代都不停息。谭其骧分析了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湘阴和靖州等地方的氏族历史材料,认为“湖南本省得五十五族,仅后于江西,超过其他一切外省,良以境土密迩,迁徙便利,此为当然之现象。”(谭其骧1987:325)
湖南西南部新化、安化一带的湘语,可能是宋朝才扩散过去的。“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熙宁五年,遂檄谕开梅山。……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宋史》第四九四卷的列传第二五〇篇)
湖南西北部南县的湘语到民国时期才形成。清朝末期,在洞庭湖北岸,长江水流携带到洞庭湖的泥沙淤积成一大片三角洲。这些肥沃的土地,吸引了省内众多移民。但是移民来源比较杂乱,各自说自己原来的方言。到民国时期还是既没有内部地位特别的方言可以推广,也没有外部一致的方言可以模仿。但是因为迁移到这里来的人的原籍一般是益阳、长沙、岳阳、常德、衡阳。益阳来的人最多,“风俗益阳化”明显。(张伟然1995:73)所以,今天南县湘语也最接近益阳湘语。
湖南省边远区域的汉语方言最晚传播过去,又最先被省外来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同化和覆盖。当湖南周围的方言都不同程度地被其他方言取代以后,湖南中部还保留了比较典型的湘语。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娄底等湖南中部的大城市的方言会形成自己的向心力。这种地域优势带来的方言优势也会使湖南核心区域的方言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长沙这样最核心的城市,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外来方言的影响很强烈,所以反而比中部其他地区的方言变化更加快,但是由于自己的地域优势形成的方言优越感的作用,没有湖南周边方言变化快。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的形成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汉族人南下和军人驻扎;第二,湖南跟贵州、广西等交界地区的自然交往。当外来的叫做官话的北方方言成为当地交流的强势方言的时候,就可能取代当地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在湖南永州和郴州还存在双方言现象,就是城市基本上被官话覆盖,没有当地固有的土话,但是农村里,甚至在江永的等偏僻的县城还保存了土话,形成土话和官话并存的双方言生活。其实直接影响湖南方言的官话,更多的是跟湖南西边和南边通行的西南官话。这是老百姓直接交流的结果,由于官话更加容易明白更加通行,人们就会逐渐自动改说官话。
早在秦朝,就有北方军队进入湖南境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军队到湖南。《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他“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现在湖南的靖州),一军守九嶷之塞(现在湖南的宁远)……三年不解弛弩。”以后汉朝、明朝派遣军队到湖南都有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篇记载:东汉建初年间,在平定武陵蛮的分支溇中蛮后,“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元史·刘国杰传》记载:“宋尝选民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到明朝发展到了顶峰。那时有“国家镇守四方之垦屯军政机关”,机关管理的士兵一般来自外地,遇到战争上战场,平时耕种。(谭其骧1987:322)
这些军人长期在驻扎地区生活,他们的语言如果是弱势语言就可能被当地语言同化。“边城父老旧乡邻,弭节从容问所因。绿鬓已应辞故里,白头犹解识先人。衣衫尚有唐风旧,童稚皆传楚语新。”(《敬轩文集》第八卷的《过沅州见故乡父老从戎者与道家乡事多有识先人者因赋此》)可见军人的后代就已经被当地“楚语”同化。
这些军人的语言如果是强势语言,就可能保持自身官话。道光《永州府志》引用旧的地方志说:“州县各在乡谈,听之绵蛮,侪偶相谓如流水,男妇老幼习用之,反以官话为佶屈。惟世家子弟与卫所屯丁则语言清楚,不类鴃舌。”
从汉朝开始,由于封建王朝多数都在中原建立都城。因此,中原战争祸害到处引发,百姓流离失所,开始向南方寻求安身地方。谭其骧说(1987:301):“中原人之开始大量来移湖南,湖南之始为中原人所开发,其事盖促成于莽末更始之世。方是时中原大乱,烽烟四起,田园尽芜,千里为墟,百姓皆无以为生,必有南阳、襄阳诸郡之人,南走避于洞庭、沅、湘之间,筚路蓝缕,以启此荒无人居之山林旷土也。”根据《续汉书·郡国志》记录,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永和五年)间,长沙国户数增长了5倍,人口增长了4倍。零陵郡户数增长了9倍,人口增长了6倍。桂阳郡户数增长了4倍,人口增长了2倍。武陵郡户数和人口数均增加了30%多。然而这140年间全国户数和人口数却反而减少了20%。可见当时湖南境内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不是属于自然增长,而是与北方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原地区向南方大举移民的第一个高潮从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开始。当时江南相对安定,许多中原人过长江避难。“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东晋统治者为了安定民心,曾经根据士族和民众的原籍设立行政区域,安排移民。当时江苏接收的中原移民最多,其次是安徽,再次是湖北、四川、河南南部、陕西北部和山东北部。然而湖南,因为距离中原比较远,只有在北边一小部分地区有移民来(谭其骧1987:211)。根据《宋书·州郡志》和《晋书·地理志》,当时设置的北方移民区域在现在湖南界内的,有南义阳一郡,南河东半郡。这次移民应该对洞庭湖一带的古代湘语造成了冲击,逐渐形成常德一带的官话。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这说明在唐朝中期,从湖北荆州到湖南常德一带因为移民而增加了户口10倍以上。唐朝末年的诗人韦庄也在《湘中作》中说:“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北方居民迁徙规模大,人数多,地域相对集中,使他们的语言不仅难以被本地土著语言同化,反而给当地土著语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就强化了常德方言的官话基础。周振鹤、游汝杰也说:“如此大量的移民势必带来北方方言的巨大冲击,以至北方方言取代了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的固有方言。常德地区的官话基础也许在此时已经奠定。”后来经过经过宋朝300百年的发展,“北方话终于由北向南逐步扩大至整个沅澧流域。”(周振鹤,游汝杰1985)
北方汉语的南下也给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造成了冲击。中原地区相对比较先进的生产力与文化促使少数民族居民自觉地向他们学习。刘禹锡曾经在他的诗《武陵书怀五十韵》中描绘他贬谪在朗州(现在的常德)的时候,“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隋书·地理志》有描绘当时“蛮”的情况,“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夏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
由于缺乏文献的记载,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南部地区的官话具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张伟然(1995:66-67)认为,湖南南部官话与宋朝到明朝时期军队驻扎有关,开始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流通。可以肯定,至少清朝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使用官话了,因为清朝到民国的一些地方志明确记载已经有了官话。例如光绪《兴宁县志》记载“民多汉语,亦有乡谈”。道光《永州府志》:“所说皆官话,明白易晓,其间不同者,则四方杂迹,言语各别,声音亦异,其类甚多。”清朝同治《江华县志》记载:“邑人何景槐曰:江邑所说皆官话,明白易晓。其间不同者,由四方杂迹,言语各别,声音异其类,甚多能悉记。”
湖南省外部的官话肯定也会影响湖南官话的形成。周振鹤,游汝杰(1985)认为湖南南部的官话是从广西传过来的,“一支北上靖州,结合湖北的影响,使靖县方言官话化,使会同、通道、黔阳方言带有湘语北片特征。另一支自西向东进入湘南,与湘语、赣语接触、交融,形成几类方言混杂的局面。”范俊军(2000)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官话在湖南南部是后来出现的,最早也只能在明朝末年以后从中国西南经过广西北部进入湖南南部。从郴州市范围来说,官话最先从西经过湖南永州市进入郴州市的桂阳县,再向东边扩散到郴州、郴县,再向南边扩散到临武、宜章甚至广东北部。”
总之,官话分布在湖南西部和南部边远区域,还难以渗透到湖南中部的核心区域。为什么官话容易在湖南外围的西部和南部形成呢?第一,这些区域没有形成一致性比较强的非官话方言,任何一种固有方言都难以成为强势方言。第二,数量多特征复杂的固有方言区域之间也迫切需要一种容易流通的官话来做为区域共同语。第三,这些区域外围的强势方言是官话,人们自然会通过跟湖南省以外的贵州、广西人交往,因此必须掌握也自然容易学会这些地区说的官话。
赣语
关于湖南省赣语的形成,周振鹤,游汝杰(1985)认为是江西移民大量进入湖南的结果。张伟然(1995:66-67)做了进一步论证。历史上有“江西填湖广”的说法。如果说唐朝以前,到湖南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那么五代以后主要来自东方。“赣、湘境地相接,中无巨山大川之隔,于是自密趋稀之移殖行动,自然发生矣。故江西人之开发湖南,鲜有政治的背景,乃纯为自动的经济发展。”(谭其骧1987:321)可见,赣语的形成跟自然移民有关,而没有政治避难的原因。
根据谭其骧考证,五代时期江西一共有22族移民到湖南,18族在湘阴,4族在宝庆府(今邵阳),3族在新化,1族在武冈(谭其骧1987:339)。宋代在湖南的江西移民很多,“这些江西人多迁自隆兴府(治今南昌市)、吉州(治今吉安市),主要从北面的修水——汨罗河谷进入洞庭湖平原,从中部今浙赣线所经的湘赣大道入潭州(治今长沙市)、邵州(治今邵阳市),从南部上犹江——耒水河谷进入湘南的郴州、桂阳军、武冈军一带。”(葛剑雄等1993:315-316)《明太祖实录》第二五〇卷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周振鹤、游汝杰(1985)总结了江西人向湖南迁徙的几个特点。第一,江西移民从湖南东北向西南、西北、东南3个方向递减,和各地距离江西北部、中部的远近成正比。因此湖南的赣语片自然紧邻江西,而且北部的赣语特征比南部更加明显。第二,江西移民的出发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泰和、吉安、吉水、安福、南昌、丰城6个县。这与江西本省各地开发程度有关。开发程度高的这6个县田没有闲置土地,但是有闲人,就自然会寻求移民的出路。然而江西南部本身开发程度比较低,自然不会向湖南移民。第三,湖南北部的移民来自江西北部,湖南南部的移民来自江西中部。这样就造成湖南北部和南部赣语的差异。第四,江西移民从唐朝到宋朝到元朝的700多年里持续增加。首先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湖南东部形成赣语,后代的移民就越过这个区域向纵深发展,深入到湖南西南边界,从湘阴到宁乡到新化到绥宁。
地方志中也有大量江西移民的记载。例如康熙《浏阳县志·拾遗志》记载:“浏鲜土著,比闾之内,十户有九皆江右之客民也。”民国《醴陵乡土志》记载:“县境之内,率多聚族而居,在数百年前皆客民也。……醴陵近江西,故族姓亦以来自江西者为多。”
一些历史记载还可以说明湖南的赣语在宋代似乎还没有完全形成。南宋词人刘克庄从江西萍乡进入醴陵后曾经说:“市上俚音多楚语。”(《后村大全集》第三卷的《醴陵客店》)这说明南宋时期醴陵与萍乡方言的差距还明显。当时醴陵还说的是“楚语”,就是湘语,赣语还没有完全形成。
客家话
客家人一般是明朝到清朝时期从广东、福建或者经过江西辗转进入湖南的,而且一般以家族为单位进行迁移。(陈立中2003:7-33)根据各地族谱的记载,客家人最早进入湖南是在宋代,大批迁移是在明朝到清朝。例如,茶陵江口黄姓的一支,他们的始祖在1184年(南宋淳熙十年)从江西赣州迁移来的。平江县最早一批客家先民是1472年(明朝成化七年)从广东龙川迁移来的。清朝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客家人先后从现在的梅州、惠州、大浦、平远、蕉岭、乐昌迁移到平江。浏阳客家人的祖先大多来自广东东北部和福建西部的汀江流域,主要是广东平远、兴宁、梅州等县市。明朝初期和清朝初期,福建客家人大规模迁移到醴陵,广东客家人迁移到汝城。炎陵县的客家移民主要是清朝来的。
客家人进入湖南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江西“棚民”因为官方捕捉被迫迁移。根据《醴陵县志》(1948年)记载,客家人“习劳尚武,男女并耕,结棚而住,故称之棚民。明亡,常纠集勇壮,头裹红巾,响应郑成功、金声桓以图恢复。……自是清吏之于棚民,捕杀之余,继之以驱逐。棚民既不容于宜春,多散居邻县”。第二,沿海居民因为战争骚扰被迫迁移。根据《醴陵县志》(1948年),“顺治间,郑成功据厦门,屡侵掠沿海诸县。清兵追之不能胜,乃颁令迁沿海之民于内地,尽焚其庐舍器物,以绝郑氏海舶所用钉铁蔴油硝磺粟帛。闽粤之人家破流亡,千里远来”。第三,政府引导移民来湖南开荒。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境内战乱频繁,导致人口急剧减少。根据同治年间《攸县志》记载,“明末兵灾,民窜田荒。”政府“招徕开垦,难敷额数”。政府为了休养生息,鼓励拓荒生产,所以有大量客家人迁移到湖南开荒。
总之,湖南客家话分布区域不大。由于客家人迁移到湖南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大多是家庭式的迁移,因此客家话在湖南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分布,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几个县市。
土话
土话包括湘南的“土话”和“平话”,湘西的“乡话”。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土话的形成过程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是可以初步肯定,这些土话由于地理位置相当偏僻,交通非常闭塞,因此种类繁多,具有早期湘语等方言特点,而且本身由于语言接触发生很多特殊变异。
梁敏、张均如(1999)认为平话“是来自各地移民的不同方言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彼此交流、融合发展,并受壮侗诸语言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我们姑且称之为古平话,在官话和粤方言进入广西之前的一千多年间,古平话曾经是湖南南部和广西南北各地百姓的主要交际用语,也是当时官场和文教、商业上的用语”。李冬香(2006)认为湘南土话是不同时期汉族移民的历史沉淀以及同当地土著民族互相影响的结果,而且到宋朝已经基本完成。(鲍厚星2004)认为湘南土话的形成原因很复杂。第一,湘南土话区域处在五岭山脉中,地理情况很复杂。第二,历代移民情况复杂。第三,与当地少数民族频繁接触情况复杂。第四,宗族势力的影响复杂。
从移民历史角度来考察,从汉朝一直到近代,湖南东南部都接受了大量的移民,而且从族谱来看,大部分来自江西,与湖南其他地区的移民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只从移民情况无法解释湘南土话的形成。而且从语言特征来看,有的相当古老,比如古代知组声母现在读塞音,江永桃川土话把“树”叫做“木”等等,可见有不同时期的历史沉淀。有的很奇怪。例如从大地岭土话的人称代词来看(彭泽润2002),几乎无法找到它跟一般的汉语方言的对应关系。这说明在语言接触的历史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许多地方不同的族姓说不同的土话,说明有家庭式移民的背景。偏僻又复杂的地理条件,造成交通闭塞,大范围地交流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最终形成了数量多、流通范围小的不同的方言格局。
湘西土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怀化市的沅陵、辰溪、溆浦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和古丈。这些县份本来就偏僻,而乡话又只分布在这些县份中交通更加闭塞的偏远山区,城镇一般通行官话或者湘语。
根据杨蔚(1999:2-3)的研究,乡话分布的区域在历史上曾经是少数民族活跃地区。当时的人被叫做“五溪蛮”。早在公元前202年(汉朝高祖五年)设置沅陵县,属于武陵郡。因此汉族人迁居这里的历史比较久远。《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注释说:“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庐山郡,槃瓠之地也,杂处五溪之内。”秦朝汉朝时期,中央政权为了平定这里,都曾经征讨过这里。公元49年(汉朝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伏波将军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根据萃默齐《说蛮》记载,“马伏波遗兵十家”,“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后发至三百余户”。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也记载“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自相婚姻,有二百余户”。隋朝唐朝时期,现在沅陵、泸溪、辰溪等地为是军事重地,当时有大批汉族人随军来到这里,因此当时文教事业一度很发达。宋朝嘉祐三年,政府在沅陵明溪口派驻军队防守,并且分给士兵田地时代(世代)耕种。元世祖开通京都到云南的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当时的沅陵、辰溪、泸溪境内设置了界(有一“亭”字)、马底、船溪等驿站。这就促进了商品流通,也吸引了一批来自浙江、福建、江西的移民。明朝到元朝,政府继续驻扎部队,让士兵世代耕种田地,吸收移民。根据1874(清朝同治十二年)守忠等编辑的《沅陵县志》记载:“县之四塞山川险峻、故元明以来他省避兵者卒流徙于此,今号称土著者原籍江西十之六七,其江浙豫晋川陕各省入籍者亦不乏”。从族谱来看,乡话区域的一些大姓氏都来自外省,主要是江西。
这些历史特征跟湘南土话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移民语言在跟当地语言接触以后在山区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独立保持和发展的结果。本来这些土话再土也不奇怪,但是在双方言区的官话的参照下就显得奇怪了。
湘语溯源
编辑 播报古楚语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语”
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栖息生活在湖南境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境内不断发现有旧石器文化遗址。1992年在石门县燕儿洞遗址首次发现的“石门人”化石,距离现在大约2万年以上。
上古时期,湖南境内主要居住有“三苗”部落。《史记正义》记载:“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三苗在跟华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以后,逐渐衰败,也没有再在历史上留名。
后来,三苗部落生长区域,建立了楚国政权,历史上叫做“荆蛮”。《诗·小雅·采芑》就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楚国的先民据说是中原祝融部落,姓芈。《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他们在夏朝到商朝时期往南迁移,一直到周朝初年,才开始定居到楚。经历几百年的经营,征服了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不过楚国一直被北方政权轻视,楚国也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南下的北方夏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结合,最终形成一种既与中原文化联系又保持自身特征的楚文化。
楚国对湖南的控制,从战国时期开始。“战国初,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取洞庭、苍梧之地,于是湖南之东部湘、资二流域入于楚。其后复西向并吞沅、澧二流域,曰巫中,而湖南之全部皆入于楚矣。”(谭其骧1987:300)
楚国地理位置特殊,它的语言跟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可能都在楚国进行过接触。因此楚国的汉语应该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别具一格。最初这种语言可能与华夏语言差异不大。虽然楚国政权建立后,一直与中原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彼此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楚国原来的居民是少数民族,楚国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必定会加速与这些民族的交流和融汇。这种新变化的汉语我们可以叫做“楚语”。
上古汉语使用范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但是今天的吴语、湘语、粤语也开始播种和萌芽了。古代楚语包括湖北、湖南以及周围的长江中游一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楚语是今天湘语的前身。(袁家骅等1983:19)
古代楚语的原始面貌无法考证,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记载中窥探它的一些特征。“楚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左传》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令尹(相当宰相的官员)子元讨伐郑国,“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可见当时楚国人说的语言已经叫做“楚言”,与中原诸侯国是有区别的。《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在讥讽楚人许行的时候也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但是既然许行能够“自楚之滕”去宣扬他的学说,而且能与“自宋之滕”的陈相兄弟进行交流,所以当时的楚语虽然与北方中原地区的语言有差别,但是仍然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
古代楚语与北方汉语的差别可能主要体现在词汇及其语音上。宋朝黄伯思《翼骚序》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左传·宣公四年》在解释楚国子文的名字的时候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可见,汉语中相同的意思在楚国的表达中有很多不同。《楚辞》中的语辞“兮”、“些”也可以当做古代楚语在语法上的特征。不过这时的楚语做为汉语应当是指流行于当时楚国上流社会的语言,也许可以叫做楚国的共同语,而普通百姓大多数还是少数民族,一般不会说汉语,还是说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
汉代南楚语
汉代的“南楚语”
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代楚语到了汉代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汉朝扬雄的《方言》中可以反映出来。下面是《方言》中与“楚”地有关的地名,先排列地名,后排列数字,数字表示这个地名在《方言》中出现的次数。资料来自丁启阵的《秦汉方言》,我们做了整理。可以把《方言》里面出现的地名分成3个类别:(1)“陈楚”为主的名称:楚42/陈楚江淮之间9/陈楚之间5/楚郢以南2/陈楚2/荆楚1/楚部1/自楚之北郊1/楚以南1/陈楚之郊1/陈楚之内1/自关而东陈楚之间1/楚颍之间1。(2)“南楚”为主的名称:南楚27/南楚之外11/南楚江湘之间7/南楚江淮之间6/南楚江沔之间2/南楚之间4/南楚宛郢1/南楚洭瀑之间1/南楚以南1/陈楚之郊南楚之外1/南楚江湘1/陈楚之间南楚之外1。(3)“江”、“湘”为主的名称:江湘之间8/江沔之间2/沅澧之间2/江沅之间2/江湘郊会1/湘潭之原荆之南鄙1/湘潭之间1/江湘之会1/九嶷京郊之鄙1/九嶷湘潭之间1/沅澧之原1/沅湘之间1/江滨陈之东鄙1/湘沅之会1/楚郢江湘之间1。
先看第(3)类地名。这里涉及的地名比较具体,容易确定。“江”就是现在的长江。“湘”就是现在的湘江。《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流经零陵县、洮阳县、泉陵县、重安县、酃县、阴山县、醴陵县、临湘县、罗县、下隽县,北至巴丘入于江。”“沅”就是沅江。《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出牂牁且兰县,流经镡成县、无阳县、临沅县,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就是澧水。《说文》:“澧,水出南阳雉衡山,东入汝。”《汉书·地理志》曰:“充县历山,澧水出焉。”《水经注》:“澧水出武陵充县西。”“潭”就是从湖南西南角发源的广西境内的融江。晋朝郭璞《方言注》:“潭,水名,出武陵。”《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镡成县下有潭水。”《汉志》:“武陵郡镡成县玉山,潭水所出。”汉朝镡成县的县治在今天湖南省靖州西南。“沔”就是湖北的汉水。《水经注》:“汉水出陇坻道县嶓冢山,初名漾水,东流至武都沮县,始为汉水,东南至葭萌,与羌水合,至江夏安陆县名沔水,故有汉沔水之名。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又东过三澨,水触大别山南,而入江也。”“九嶷”就是湘南的九嶷山,在现在的宁远县城东南。《山海经》第十四:“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方言注》:“九嶷,山名,今在零陵营道县。”这些地名,除了沔水,都在湖南境内。
再看其他两类。第(1)类主要涉及“楚”和“陈楚”,第(2)主要涉及“南楚”。“楚”和“南楚”的关系到底怎样?“南楚”是“楚”的南部,还是它南方的独立地域?我们认为广义的“楚国”应该包含“陈”、“楚”和“南楚”。狭义的楚国就是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楚”。“楚”和“南楚”虽然在权利管辖方面不是并列关系,但是至少在方言不同方面是并列关系,因为扬雄的《方言》本来做为一部提供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的著作,在讨论方言不同的时候,经常把“楚”跟它南边的“南楚”和北边的“陈”并列使用。《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楚顷襄王21(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朝将领白起率领军队攻破楚国都城郢(现在的湖北江陵北部),楚国被迫把都城迁移到陈城(现在的河南淮阳)。所以“陈楚”应当指“陈”和“楚”,包括现在湖北的大部分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南楚”多与“江”、“湘”等并举。《史记·货殖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里的“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当指当时的4个诸侯国,包括现在湖南、江西的大部分以及湖北、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楚国都城郢就是在湖北和湖南交界位置的长江边。可见,“陈”、“楚”和“南楚”是把长江做为中心从北部到南部的3个连续区域。